堅守40年,他負債造出全世界最高的植物園
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,
位于3340米的滇西北橫斷山脈,
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植物園。
成立22年至今,
搶救性地遷地保護了超過400種
當地特有的高原植物,
其中不少已經位于滅絕警戒線下。


▲
高山植物園不同季節時的景觀
創始人方震東今年58歲,
從事植物工作40年,
是著名的滇西北植物及植被生態學家。
當年,賬上只有4萬塊錢,
他靠拼命接活,四處籌錢,
建造起中國第一家
由民間非營利機構管理的植物園。
他在乏人問津的高原,
孤獨、倔強地守住一株株植物。

▲
方震東在海拔4800米的沙魯里山脈
方震東說很少的話,
聊起植物會露出孩子般的笑容,
爬4800米的高山,如履平地,
把年輕人遠遠甩在后面。
我們去香格里拉找他,
一個人如何花去大半輩子的時間,
只為這一件事?
為什么給植物建一所諾亞方舟是如此重要?
自述:方震東
撰文:洪冰蟾
責編:倪楚嬌


▲
水母雪兔子

▲
三指雪兔子

▲
葉咢龍膽

▲
波密紫堇

▲
綿頭雪兔子
國內多數植物園,以科研為主,但我把高山植物園,定位成香格里拉的“后備花園”。
很多珍稀物種,全世界只有在這里的野外才找得到。所以滇西北這一塊被認為是低緯度、高海拔的物種基因庫,是第三紀古熱帶生物區系的避難所和活化中心。
人為的過度采摘,土地利用格局改變,比如建設水庫和礦場,還有全球氣候變化,我擔心香格里拉高原上的一些物種會因此滅絕,就把部分野外的植物遷地保護到植物園里,給它們一個安全的、可繁衍后代的環境。
如果當真有一天,野外的物種消失了,那我這里有一個存檔,能把植物園里的物種散播出去,到野外重建和恢復它們的居群。

▲
高山植物園內的瞭望塔和袞青寺遺址

▲
植物園試驗田種植的中甸刺玫
比如香格里拉特有的中甸刺玫,原本屬于極小種群,野外居群數量低于500株,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。
我在一個水庫庫區找到了它,那個范圍里總共只有500株左右,其中300多株位于淹沒線以下。我覺得再不保護來不及了,就收集它的種子到植物園里育苗。

▲
方震東在溫室,檢查植物生長情況
我們保護成功的標準是“從種子到種子”。找到它們,等它們結果,收集種子,到在植物園里育苗,再等開花結果,下一代的種子能夠生長,才算一個完整的周期。
保育的每一步都會有意外,要不斷地從頭來過,原本已經很漫長,放到高原上就更加長。
香格里拉的氣候從溫帶到寒溫帶再到寒帶,植物的生長很緩慢,像高山上的雪靈芝,長到直徑20公分,看上去小小的平平無奇的一個墊狀體,已經用去上百年的時間。
好在中甸刺玫現在每年能繁育幾千株到上萬株的小苗出來。可以說,已經把香格里拉的市花拖出滅絕的警戒線了。這個過程,我花了十年的時間。

▲
方震東在植物迷宮區

▲
園區內的黃褐鵝膏

▲
擬秀麗綠絨蒿

▲
西藏杓蘭
現在,園子里已有620種原生的高等植物,遷地保護了400多種野生植物,不少于200種菌類,100多種鳥類。苔蘚地衣、昆蟲還在統計中。野生動物也正在回歸,比如珍稀動物毛冠鹿,國家二級保護動物豹貓和豬獾。


▲
方震東和兒子方曄在野外考察
我出生在迪慶維西縣,在瀾滄江邊嬉戲長大的,我們算是中國西南最邊境的漢族。
1981年高考,我是迪慶州的數學單科狀元,當時夢想成為陳景潤那樣的數學家,就報了云南大學的數學系。結果接到一個生物專業的錄取通知書。
過了將近20年,我們當地的一個領導問我,你知不知道你的志愿怎么被改的?我才知道他們當時認為,我們州缺少生物方面的人才,他親自幫我改掉的。

▲
1986年在茨中做香料資源調查

▲
1993年在尼汝采集蕨類標本
當時的政策是從哪里來回哪里去,1986年,迪慶州成立了高原生物研究所,我就被分配到香格里拉,成了所里第一位科研人員。
那個時候香格里拉還叫中甸,沒有旅游開發,人煙稀少,只有一條老214國道穿城而過。剛來的時候高原反應,冬天刺骨的冷,條件很艱苦。
我第一個任務,就是全迪慶州的野生花卉調查。花了五年時間,我走遍卡瓦格博雪山,白馬雪山,干暖河谷,虎跳峽,主要靠兩條腿。
直到現在這個年紀,我一年還是有2-3個月在野外考察。
我的作息是跟著植物走的,春天播種,秋天采種。挨餓是常有的。以前在山里迷路,身上的糧食吃完了,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村子,村民們自己都還是半饑半飽,沒有糧食可以賣,喝了幾杯水睡了,夢里都是雞鴨魚肉,第二天醒來還在流口水。危險的時候也有,撞上過黑熊,就在我背后經過,所有人都嚇傻了。

▲
人工培育的蓮瓣蘭-紅心紫荷
也是在這么多年的走訪中,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。
80年代,我隨便走到哪一個山谷和鄉鎮,都很容易采集到蓮瓣蘭。但是經過90年代的蘭花狂熱,外來的商販來收購當地的野生蘭,老百姓熟門熟路,都知道哪座山上有,就去挖來交給這些商販。我就看到人們一卡車一卡車地拉走蘭花,資源就在手上流失了。
后來,我再到同一個山谷里去,幾乎已經找不到蓮瓣蘭了。
我覺得刻不容緩。剛好1999年,納帕海邊的一座山在挖沙采石,被叫停后,留下了十幾個大沙坑,我就想著,要不在這里建一座植物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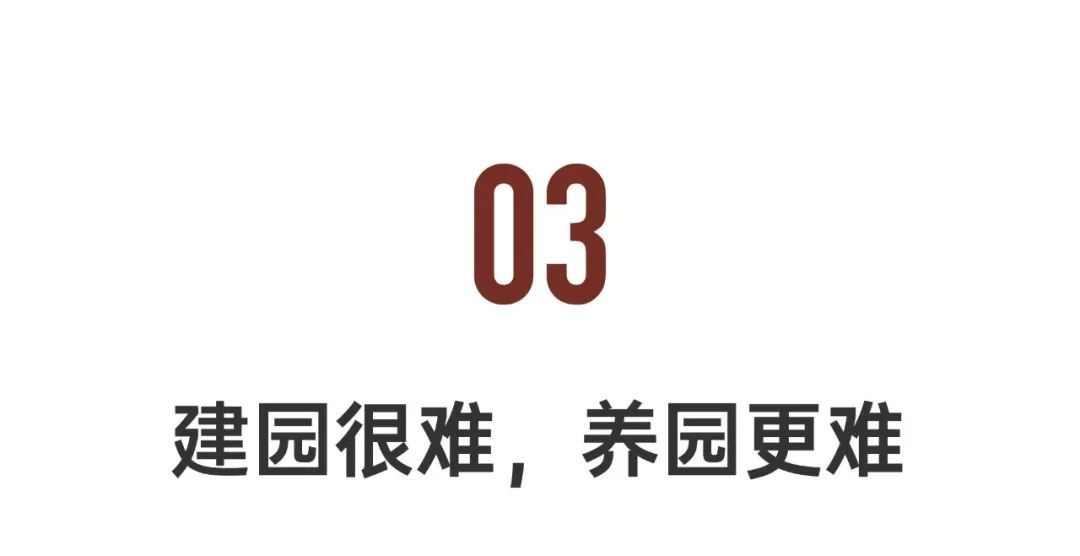

▲
方震東在苗圃區
建一個植物園要花多少錢?上億是很正常的。2000年的時候,我計劃了一個4000多萬的預算,跑去問領導,他們很頭疼,說沒有一筆錢可以給你建植物園用的。
我當時賬上只有4萬塊錢,籌建辦全部的身家。我就拼命地接活,比如聽說有種苗工程的資金,我們就用這筆錢建苗圃,有一點錢,就造一點園。
常言說建園容易,養園難。
運營植物園很費錢,最困難的時候,又要維護保育的植物,員工的薪水遲遲發不出,還拖欠了施工隊的工程款。我就到處問親戚朋友借錢,把家里“洗劫一空”。
我的同事說我們方園長,不會張羅,不會求人。因為我性格很內向,不喜歡說話,植物也不說話,所以我喜歡跟植物打交道。但是因為植物園,就硬著頭皮去跟上級部門,跟老百姓接觸,也沒辦法,臉皮厚了。
2010年,我打聽到一筆藏區專項基金,又跑去訴苦,得到了國家的資金支持。植物園成立十年,才終于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工程內容。我終于不用到處跟人借錢了。

▲
9-11月是采種時節,在樹下綁一個網兜,把種子收集起來
最開始在植物園里育苗,死的多,活的少。
我們跟老鄉收牛糞做肥料,調配土壤比例、噴灌頻率,人工除草,先在大棚里養活了,再移到戶外的“練苗區”,相當于一個實習階段,讓植物適應自然的環境,再把能存活下來的栽到其他地方。
有時候花了3年心血,幾千個工時,移到外面,一夜之間全死了,負責照料的同事蹲在田里,看著枯萎的葉子掉眼淚。
還有些種子的組織,帶有非常細碎的絨毛,會粘在呼吸道上,每年采種季節,總有一批同事感冒病倒。這些年我們慢慢摸索出植物的生長習慣,存活率提高很多。別的地方遇到怎么都養不活的植物,還會來喊我幫忙。

▲
朱紅大杜鵑
保護工作跟當地老百姓有很密切的關系。
很多極小種群,就長在村莊附近。其實早在19世紀,外國的植物獵人就來滇西北,把本地特有的植物采集回去做研究和馴化,但是當地人還沒意識到這些植物的價值。
2015年,我去騰沖找朱紅大杜鵑。當年植物獵人把它從我們這里引種出去,和其他杜鵑雜交,培育出了30多個品種,這個花在國外非常出名,在原產地卻消失已久。

▲
龍江邊僅存的幾株朱紅大杜鵑
第一年,尋找的路線不對,沒有找到。第二年,我們從大岔河的河谷底部往上找,發現最適合生長的區域已經建了水庫,很多株群已經被淹沒,幸好淹沒區之上還長了一些。然而,因為氣候土壤不同,在園區培育的苗始終長不大。
我就想繼續在野外找,就四處托人問。我在騰沖遇到了小張夫婦,他們說這種植物好像見過,哥哥家的院子里好像就種了一株。當時不是花季,我請他看到開花了就通知我。有一天,小張給我打電話:“開花了,你們來吧。”第二天我就出發,還真是朱紅大杜鵑。
在整個騰沖龍江流域,我只找到六株朱紅大杜鵑。然后我就請小張夫婦在當地的苗圃種,他們非常有責任心,已經養了100多株出來。這幾乎是我們培育出來的全部了,很小的數量,遠遠沒有超過極小種群的最低警戒線。

▲
小葉栒子
植物園的理念是兩個部分,對于這類珍稀物種,以繁育實現保護;對于有經濟價值的,比如藥用、園藝用的物種,以繁育實現利用。
園區里零星散落的結著紅色果實的矮灌木,是1999年,我去拉薩的途中遇到的小葉栒子,當時培育出第一批苗,隨意種在沙坑邊上,過了十幾年,它竟然長出了茂密的一片。


▲
當地特有的中甸山楂、中甸冷杉
有時候去不同緯度的城市,感覺很同質化,連行道樹都一樣,很多地方做市政工程、生態修復,會移栽很多外來的樹,撒一些外來的草種。我也在思考,我們滇西北生物多樣性那么豐富,為什么不用本地的植物?為什么不讓每個城市有獨特的植物景觀?
然后我就把小葉栒子這個植物當作示范,把它用于城市里的園林綠化,以及去覆蓋野外裸露的地表,恢復當地植被和區系。

▲
方震東和團隊在雪山上,帶著科考狗綠豆
除此之前,我還承擔了全球高山氣候與植被變化監測(橫斷山脈段)的工作。這15年來,我們團隊每隔7年,到高山上做樣方,監測地溫和植被變化。
這背后是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假設:高山頂部的物種會不會被擠出高山孤島?因為氣溫升高,一些低海拔的物種會逐漸上移,搶奪原本頂端物種的棲息地。這個就像華山事件,當游客不斷往上擁擠,原來站在頂上的人可能會墜入懸崖。
我們剛完成第三次監測,植物的變化現在還難以判斷,但數據顯示地溫正在升高,以前香格里拉10月份就下雪了,到了2000年以后,得等到春天才有降雪,冬天干旱的現象頻繁發生。

▲
高山植物園面朝納帕海
雖說是我不用再借錢了,但植物園還是有很重的運營壓力。
我們也設置了門票,20塊錢,但沒什么游客來。我們其實就在香格里拉著名景點納帕海邊,游客去那里玩,騎一次馬都要180塊。
我們主要的錢都花在保育和科研上,沒有那么多錢去做觀賞性的游覽和網紅打卡點。導游也不大愿意帶游客過來,這里沒有旅游產品賣。
我每年都會種大片的郁金香,投入十幾萬,門票收入兩萬塊,又累又虧本。但是郁金香觀賞性強,還是堅持種,吸引大家來植物園逛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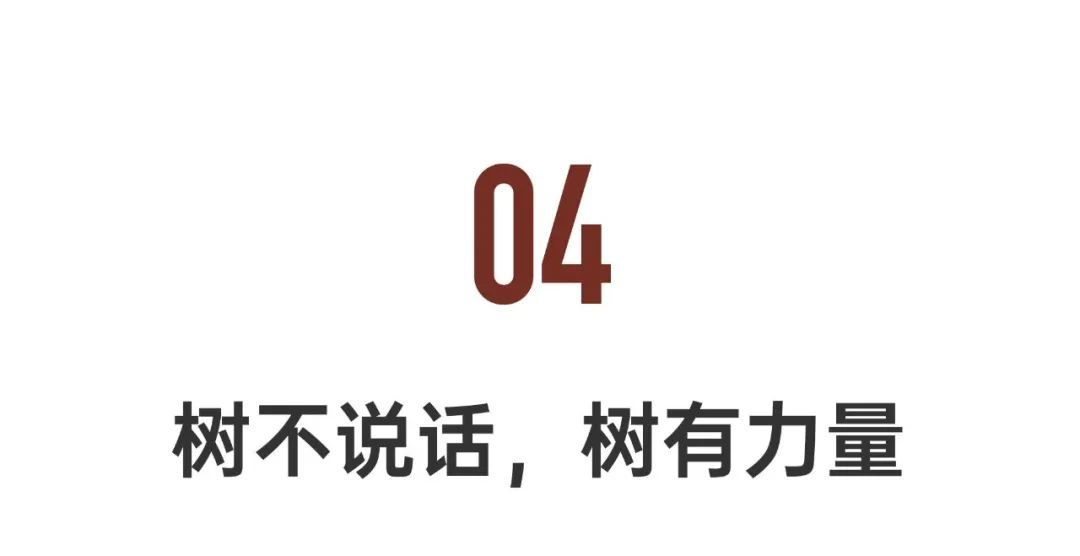

▲
方震東在觀察植物切片
接觸植物40年,建植物園我是有一點私心的。
小時候家里做飯,我要去砍柴生火,砍過松樹、山核桃樹、杜鵑花樹。我是做過破壞的人,自然而然對植物產生一些內疚感。如果有一個植物園,保護它們,我自己也能開展一些科研,算是我的心愿。

▲
海拔4500米的流石灘夾縫里,生長著雪蓮花
也是因為這一行,我才認識了妻子拉姆。參加工作后不久,我要去卡瓦格博雪山采集標本,在德欽縣碰上了拉姆和她的同伴,剛好也要去雨崩。我們就結伴同行,一路上,我教她怎么壓制標本,在4500米的高山流石灘里,拉姆第一次看到了雪蓮花,笑得合不攏嘴。
下山以后我就給她寫信,她也不說喜歡不喜歡,就來幫我壓標本。拉姆的朋友還勸她,說這個男人有什么好的,連句話都不會說。結婚的時候,我沒什么積蓄,因為經常出野外,還倒欠單位300塊錢。

▲
藏族老鄉在植物園里撒種
這么多年,植物園的團隊已經有26個人,其中有幾位,從小丫頭小伙子的時候就跟著我,現在都成了高原植物專家,孩子都很大了。
管理苗圃的劉琳,20年前,我給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野外找中甸刺玫。她找了回來,在苗圃里種下了第一棵小苗。過了很多年,它開出了粉色的花,非常漂亮。劉琳幾乎每天都去看它。前不久我想把這株樹移到其他地方,她死活不肯。她說這樹陪了她20年,她跟它有了感情,跟她的生命一樣。
和我一起長大的發小李健虎,他一打聽到哪里要土地動遷,修路拆房,就立刻出發,去救樹。兩三年前,聽說一批亮葉杜鵑、紅棕杜鵑要被挖掉,這頭挖掘機馬上要開工,邊上他還在問老鄉能不能賣樹。老鄉說,100一棵。他壓價10塊一棵。還是去得晚了,只搶救下2000多棵,運回來種在植物園里,今年開了第一次花。

▲
毛葉玉蘭
我剛剛悄悄地育苗成功了一個植物,毛葉玉蘭。
30年前,我就看到這個植物的記錄,但以為當地早就滅絕了。直到5年前,國外一個植物園的園長來香格里拉,他想來尋找毛葉玉蘭,我才知道我們州還有這個植物。我沿著他給的坐標位置去找,找了兩年才找到。光采集種子就很不容易,因為總是被蟲吃掉,我花了三年時間培育出來了66株小苗。
什么時候才會開花,基本上沒人能準確地知道。像光葉珙桐,當地人說久的要23年才會開第一次花。毛葉玉蘭,可能再等5、6年,可能更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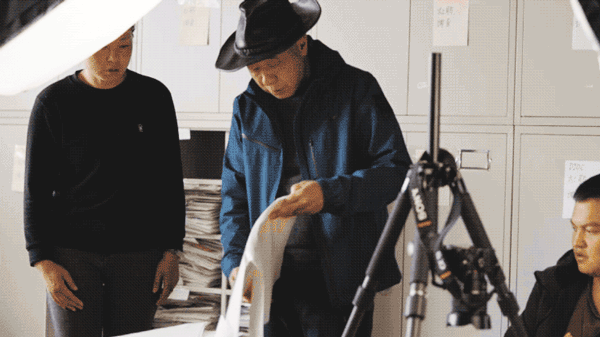
▲
方震東在指導年輕的科研人員拍攝標本
在植物界,15年算是短,100年不算長。人的生命有限,遇上生長周期很長的植物,要研究它的整個生活史,在一代的人手里面可能完成不了,要靠下一批科研人員介入。
我兒子方曄從北京林業大學畢業后,就回了植物園,我退休以后,他做了新一任的園長。我已經把手里的這些種苗交給植物園里的年輕人,他們可以繼續地觀察、培養,直到它們開花結實。
我自己還欠了很多債。趁現在還年輕一點,還有一些時間的話,我想把我這40年來的科研成果,歸納整理出來。這兩年我陸續出版了《迪慶傈僳族藥用植物圖鑒》《滇西北裸露地表植被恢復研究》,正在寫《迪慶州的生物多樣性》,未來的計劃,還是想讓更多人意識到保護多樣性的重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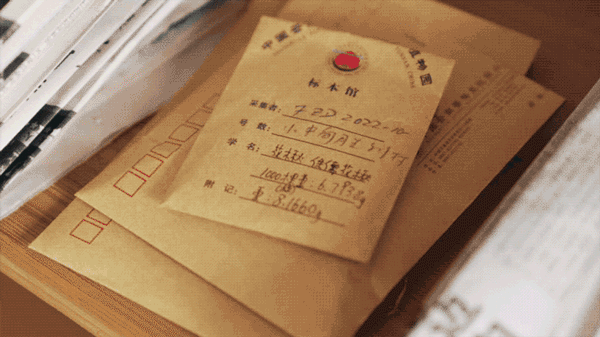
▲
他目前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寫書上
很多人問,為什么要花大半輩子去保護植物?
植物的多樣性它是一種遺產,經歷了幾萬年,幾百萬年,很多物種的壽命已經遠遠高于人類存在的歷史。我不想做道德綁架,但我想任何物種在地球上都有生存的權利。
第二個方面,植物存在的一整套原理,如果能被我們科學家理解的話,一些化學結構、次生代謝產物是可以復制和應用到其他領域的。一旦植物消失,我們就沒有機會去研究了。我一直說,保護的代價是遠遠低于重新開發的。如果沒有植物作為模板,人類要去想象一種化學結構,是想象不出來的。
我們人類吃的住的呼吸用的,都是來自于植物,那么僅僅是花了一點力氣,建了這么一個類似幼兒園一樣的地方。可能大家以為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,但我認為還遠遠不夠。

到目前為止,這座植物園,只是針對香格里拉區域來說,我們保護的速度,基本上能趕得上植物滅絕的速度。但是如果放大到青藏高原,光靠我們一個小小的機構肯定是趕不上這個變化的速度。
你問我當初被改志愿,后悔沒有?我沒有后悔,改了挺好。
部分資料由方震東和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園提供
| 版權聲明: 1.依據《服務條款》,本網頁發布的原創作品,版權歸發布者(即注冊用戶)所有;本網頁發布的轉載作品,由發布者按照互聯網精神進行分享,遵守相關法律法規,無商業獲利行為,無版權糾紛。 2.本網頁是第三方信息存儲空間,阿酷公司是網絡服務提供者,服務對象為注冊用戶。該項服務免費,阿酷公司不向注冊用戶收取任何費用。 名稱:阿酷(北京)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聯系人:李女士,QQ468780427 網絡地址:www.arkoo.com 3.本網頁參與各方的所有行為,完全遵守《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》。如有侵權行為,請權利人通知阿酷公司,阿酷公司將根據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刪除侵權作品。 |
 m.quanpro.cn
m.quanpro.cn